靈魂音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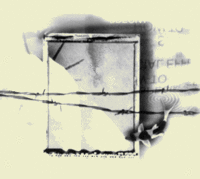
廢棄停車場就在橋的下方,城市裡一部份的廢棄車輛,不知道經過了什麼樣的際遇和旅程,最後都來到這方河床邊的空地,緊密地挨在一起,像是等待出殯的棺材。場地略呈一個三角形,前邊是環河道路和長長的河水,後邊則是高聳的灰色河堤。所有的車子,包括機車和汽車,就一列一列整齊地放在這方空間裡,展示著城市滄桑的更替。它們的沉默在囂擾的車陣間懸浮,好像隨時會滑入河水漂走,消失在下游黯淡的夜色裡。
因為走路過橋,比平時晚了莫約十分鐘到家。我看著遙遠的橋頭和橫在中間的半透明煙霧,想像著用雙腳做飛矢問題般地二分之一的切割。然而不管我走得多麼緩慢,靜靜的廢車場及光華燦爛的橋身還是從我的視野中完全消失了。
脫下厚外套掛到衣架上的時候,電話鈴響了。音響裡正放著林憶蓮的「傷痕」。我稍微遲疑了一下,還是在答錄機打開前拿起話筒。
「請問是……」對方是一個中年男子的聲音。
「我就是,請問哪一位?」我調整聽筒的方向,以減少無線電的干擾。
「請問你是不是曾報案機車失竊?」
「是的,找到了嗎?」
「什麼時候報案的?」
我想了一下,「今年四月,在某某分局報案。」
「車牌號碼呢?」
「請等一下,」我從上衣口袋拿出半年多沒用的行照,確認上頭的牌照號碼,「QPF-076。」
對方複誦一遍表示確認。
「你的車子已經找到了,隨時都可以領回去。」
我翻開行事曆發現下個禮拜才有時間。
「下個禮拜可以嗎?」
「沒問題。」對方留了地址和連絡電話,「當天請先來電確定時間。」
「好的,麻煩你了謝謝。」
掛上聽筒後我把襪子丟到洗衣籃子裡頭。
失竊的機車經過半年後,好像街上巧遇畢業同學般地出現了。我想像它失竊後可能的遭遇,包括報廢後扔在路邊、臨檢時被發現、送到機車行裡轉手賣掉,或被用做犯案的贓車。尋思及此我才想到忘了問機車是怎麼被找到的。
我繼續把襯衫、長褲脫下掛好,換上輕便的家居服,坐在沙發上發呆。正前方的三十二吋灰色螢幕裡澄淨地映著我的形像||雙腿伸直身體窩在黃綠色的沙發裡,臉頰周圍被擠出一層雙下巴。我關掉音響打開電視,一瞬間我的倒影就消失了。晚間新聞的片頭啪地破水而出。
我到廚房用開飲機沖了碗泡麵坐到客廳,在等麵條軟化的五分鐘裡我撥了通電話給他。
「車子找到了,警察局剛剛通知我。」
「真的!怎麼找到的?」
「不曉得,我忘了問。」他正在看同樣的新聞,我聽到他那裡的電視聲音。
「滿幸運的。」
「下星期有沒有空,陪我去領車吧。」
「好啊。」
他答應後我們又花了三分鐘寒暄才互道再見。我撕開鋁箔紙用免洗筷攪拌軟硬恰到好處的澄黃麵條。
* * *
機車遺失後就比較少到醫院去看奶奶。
奶奶一年前入院,本來只是胃病送醫檢查,結果發現已經是胃癌末期。沒有人告訴她病情,直到半年前她還樂觀地相信只是胃潰瘍,很快就可以出院。
上禮拜是我最後一次到醫院看她。加護病房的開放時間是晚上六點到六點半,我和父親約五點四十五分到達醫院,在門口遇見大伯父和兩位姑姑,他們也是下班後趕來這兒。奶奶在清晨六點左右曾經失去意識,中午才稍微穩定,到現在似乎已經很清醒了。
六點整加護病房的電動門打開,和我們一樣在外頭等候的家屬默然地先後進去。一個床位一次只能進去兩個人,我和姑姑先在外頭等待,不久伯父出來要我進去。
套上淺綠色的看護衣後,我走進明亮的加護病房。裡頭比外面略涼,空氣裡有著淡淡的消毒味。我找到奶奶的床位,靠到她身邊。由於癌性腹膜炎和惡液質的低營養狀態,奶奶腹水的情況相當嚴重,大量腹水壓迫著橫隔膜,使得她呼吸困難意識不清,只有藉助氧氣罩。並且因為胃壁潰瘍破裂,無法排出的血水逆著食道而上,泊泊自她臘黃的嘴角流出,在床墊上留下一片觸目的殷紅。醫生從她嘴部另插一根管子保持呼吸道通暢,她也因此不能說話。
父親看我來了便握住奶奶的手示意。奶奶微睜著眼,嘴裡吐出的氣體在透明的罩子上凝成一片白霧。父親要我握住她的手。這時我才發現她的雙手被棉布條綁在床緣的欄干上,能夠擺動的角度不超過三十度,大概是為了防止她因為太過痛苦拔掉身上的維生系統。奶奶的右手在半空中揮舞著,似乎要表達什麼。她先指我,又指著自己,最後指指前方,動作凝滯緩慢地重複進行著,然而我們卻猜不透她的意思。一個大概是醫療人員的中年女人過來檢查她身上的儀器管線。父親把奶奶的手勢告訴她,想知道是不是有什麼地方不對勁。她說只是因為不舒服,又對奶奶說了一些勉勵的話。
直到兩位姑姑也先後進去探視,奶奶的手勢似乎沒有停過。
六點半一到,門又安安靜靜地閤了起來,將我們與裡頭的世界隔離,包括身體的痛苦、精神的絕望及醫療人員間輕鬆的閒談。它們頓時從我的精神抽離,讓我因為脫出那種窒息的氣氛而像失去支持的藤蔓般地鬆了一口氣。
* * *
第二天奶奶就過世了,下班後父親打電話過來,用有點疲憊的口吻告訴我這個消息。
「在什麼時候?」我問道。
「十點左右。」
我算一下時間,我正趕著過天橋、搭公車的時候,醫院裡的奶奶身上還插著粗粗細細的管子,吐著越來越微弱的氣息;就在我打開辦公室電腦,等待PC-cillin掃描硬碟,她或許還在比著那徒勞的手勢;當我用鍵盤輸入第二千三百七十一個字元時,她八十四年的生命就結束了,一點感應也沒有,好像地球另一端一個完全不相干的人死去一樣。
隔天傍晚我打電話告訴他這件事,因為他奶奶過去的時候也跟我說過。
「有沒有很難過?」聽完我簡賅的敘述後他問道,算是安慰吧。
「沒有啊,只是有點不習慣。」
「不習慣?」
「是啊,一個本來會跟你說話、感覺得到體溫、還沒有變成記憶的人,突然從你的生命中消失了,很難一下子適應這種情形。」
* * *
頭七在半山腰的一家寺院舉行,聽說奶奶生前常來這裡燒香還願,在這裡辦頭七也是她的意思。儀式其實很簡單,就是不斷地頌經,但是時間非常冗長。尼姑們用一種似唱非唱的調子頌著金剛經,偶爾還要起身向西天諸佛躬身行禮。因為無聊我就聽著她們頌經一併閱讀經上的文字,大部份是滿淺顯的古文,除了一些專有名詞,我大致都還能理解。
儀式從早上到下午一直持續著,每頌完一卷休息半個小時,親戚們就聚在一起聊天。對於奶奶的死本來就沒有特別的哀傷,尤其是到加護病房看過她之後,我想她當時一定也有「趕快死了吧」的想法。然而那謎一般的手勢到現在我還是無法理解,有著無論如何也應該知道的遺憾。
* * *
預定的清早先打電話給警官,再次確定時間。接電話的是個年輕女子,她客氣地說「請稍待」,把電話轉接過去,經過幾秒鐘綠袖子的旋律,中年男人的聲音從話筒那頭傳過來。
「就是這樣,我六點才值班回到警局。」
「沒關係,我五點下班,我也打算那個時候過去。」
「那就沒問題了。」
「一切麻煩你了,謝謝。」
中午休息時間和幾個聒噪的女同事聊天,談論誰被什麼公司騙了,蘭寇的保養品是否真如廣告上描述地那麼清爽。「還是沒有世界末日的新聞啊」,我讀完報紙後這樣想著。太陽和月亮沒有掉下來,美國和中共也沒有引發核子大戰,更沒有可怕的疾病爆發流行或巨大的惑星逐漸接近地球。但即使到了那一天,生命還是像沙漏般地無法挽回。
一般人都以為黑暗的人生和光明的人生,是一開始就完全相悖地發展著,好像從赤道上開始向南及向北走,最後分別在南北極停止。其實人生的脆弱不是很像過節的星星燈嗎?只要串連上少了一個燈管,後頭的序列都會黯然無光。使一個人變成現今模樣的,並非過去留下過很大的傷痕,相反地它可能像星星燈上的一個燈管那樣地容易被忽略。從那小小的點開始,現實就和光明燦爛的理想分歧,甚至連從前的光芒都消失了,變成截然不同的人生。
我想我也經歷了那一個點。然而那到底在什麼時候、遺落到什麼地方去了?
* * *
下班後他開著貨車來接我。穿過長長的車流,花了約四十五分鐘的車程,前往城市另一頭一間從未去過的警局。下車後我們先到對面的便利商店買了晚餐要吃的罐頭,六點整走到位於警局後方的交通大隊。說明來意後,一個莫約三十五歲的警官前來協助我們,從口音我聽出來他就是電話裡跟我連絡的警官。他先要了我的行照和報案證明,從電腦裡印出一張表格,上頭有我報案的詳細資料。然後他請我們到一間小房間稍候,不久他和另一個警官拿著一疊表格進來,在旁邊的桌子上填寫。我看不仔細他們在寫什麼,不過一份好像是筆錄,另一份則是銷案證明吧。
我無目的地看看頭頂旋轉的電風扇,牆壁上在冬天送著風的冷氣,聽見門外有雜沓的腳步聲不斷經過。偶爾踢踢他的腳底,討論機車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。正當感到極度無聊的時候,警官又請我過去詢問一些問題,像是機車的殘餘價值這一類的,然後要我在筆錄上蓋手印。我趁機看了下內容,只是些很普通的問答記錄,像車子在哪裡丟的、什麼造型、在哪裡報案諸如此類的。
一切程序完成後,他交給我一份證明文件,因怕我們迷路又畫了一份拖吊場位置的簡圖。
拖吊場位在半公里外的一座高架橋下,需要左轉兩次,然後從橋右側的一條小路進去。他把車子停在鐵門外。我們把文件交給管理員,他核對過後說我們可以進去找自己的車子。我先走進去,他則請管理員把門打開,好讓車開進來。
「怕車子壞掉了,所以想用載的。」他這樣說道。
拖吊場呈狹長形,完全被高架橋的陰影所覆蓋,在粗大的橋墩上架著水銀燈,清冷的光線把忒大的場地割切地黑白分明。我的車子就停在最裡邊,一排又一排密無縫隙的機車行伍當中。我朝著它們前進,橢圓形的水銀燈在不同形狀的玻璃、塑膠和鋼板上流轉著,好像某種密碼,輕輕地在我眼前跳動著。所有的機車因我的出現都陷入歇斯底里的興奮,以等待主人的神色打量著我,然後失望地沉寂了,只剩我和它遙遙對望。它被放在裡頭第三排靠中間的位置,卡死在Dio和Cabin的當中。
我使勁把附近的車子拉開,好不容易才清開一條小小的通道把它拖出來,再把其它的車子移回去。整個過程我出了一身汗,雙手也被車上厚重的灰塵弄得骯髒。
被拖出來的我的機車,停在空曠的柏油地上,用一種久違的聲音向我問候著。
「好久不見,虧你還找得到我。」
我搖搖頭,「我沒有找你,是警察找到的。」
「這沒有差別,是因為你想找我,我才能被找到。」
「是嗎?」
它點點頭。
我仔細看著它,上頭的貼紙已經被撕掉,留下一片髒污的痕跡,後照鏡和置物架也被拔走,只剩空空洞洞的寶藍色車體還保持著當年的流線。
「你變了不少。」
它說道:「你也是啊,只是你看起來越來越出色了,我卻逐漸地喪失機能。」
「你這樣覺得嗎?」我不置可否地聳聳肩。
「現在做什麼?」
「還在原來的地方上班,才半年啊,總不能一直換工作吧。」
「說的也是,才分開半年,我怎麼覺得好像有半世紀那麼久了呢?」
它輕輕地笑著,就像小時了了後來卻懷才不遇的那種笑法。
「這裡的日子不好過吧?」
「沒有想像中的悲慘,大概就像你們退休以後,沒有目標地一直衰老下去吧。」
「好懷念那半年,我們一起去過好多地方。」我笑道。
「那個時候我的性能還很好喔。」
它又問道:「男朋友呢?」
「說起來有點不能相信,不過我還和同一個人在一起喔。」
「那很好啊,他一定是你真正喜歡的人吧。」
「對啊,要是能一直下去就好了。」我說道。
冰冷的夜風自我們身邊穿過,讓我感到些微的寒意。越過頭頂的高架橋,可以看見遠方成排的街燈,及像是中局圍棋般錯落的房舍燈火,那光線橫過一片什麼也不是的黑暗,溫暖地投射在我的眼底,就像是一個很古老的回憶。
「以前怎麼沒這樣聊過呢?」
「以後也不會有機會了。」它這樣說道,「只有在很短暫的時候,人生會變得前所未有的清明,就像夏至只是一年中的三百六十五分之一,而在那一天當中也只有正午時分在回歸線上的陰影會消失不見。現在就是那樣的時刻。」
大門隆隆地打開,他把貨車開了進來,耀眼的黃色車燈剎時劃開陰冷的水銀燈光,筆直地朝我們而來。
「要走了。」
它點點頭,然後沉默不語,那些微弱的密碼消失了,只剩一部冰冷老舊的機械骨架在微明的空間中幽幽漂盪。這時我才明白,已經失去的東西還是讓它永遠失去,再找回來的不再值得感傷。
我們合力把機車抬上車子,向管理員道謝,離開前管理員拿著文件過來核對引擎號碼,才把鐵門打開。
* * *
告別式早上八點半開始,我大約八點到達殯儀館,親戚們此時也陸續到達,伯父站在靈堂外頭把喪服按次發給每個人。今天比頭七來了更多人,除了本家,奶奶的娘家也有代表前來,好像是她的姐妹。大家的表情並不是那麼哀傷,但是都有說不出的壓抑。
八點半過五分,三個道姑緩緩走進靈堂,燃了一把香發給每個人,示意大家先朝外頭三拜,再朝靈位三拜,插到銅製的香爐裡頭。
我走進靈堂,順從其它人的引導,站在自己的位置上,默默地聽著姑子們頌經。
告別式在十點結束,眾人先將預備好的紙屋、紙人、紙錢還有奶奶的遺物送到大型焚化爐,投進熊熊的烈火中。爐子的溫度相當炙人,想要靠近一公尺以內大概就會焦燎而死。我們站得遠遠地把所有的東西扔進去,火舌立刻竄燒起來,濺起的飛灰頂著龐大的熱氣衝上高聳的煙囪,在頂端發出爆裂的聲響後,像是落葉飛花般的黑色灰燼在空曠的場地內四散飛舞著,撲在每個人身上,真是一幅美麗的畫面。
殯儀館的人把奶奶的遺體運到火葬場,門外早已停了五、六口棺木,奶奶的棺放在最邊上的位置,擺好鮮花和香爐,接下來所要做的就是等待。火葬場的煙囪不時冒出蒸騰的白色煙柱,靜謐地散佚在晴朗的天空當中。巧的是奶奶葬儀的日子都是冬季難得的好天氣。一切程序在下午兩點結束。奶奶的遺體火化,經過一小時的冷卻,變成小小白白的骨灰,放進只有人體十分之一大小的大理石罈子。罈子會被送到附近的靈骨塔,和爺爺及其它祖先在一起。
我還記得見她最後一面時的異和感,時間讓她變成不是我所熟悉的奶奶,以後我對我也會如此。放在棺木裡的她臉色蒼白,發脹的臉皮被擠在下巴周圍,尚未排出的腹血自嘴角流出,好像照片一樣地凝結著。


0 Comments:
Post a Comment
<< Hom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