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讀生手札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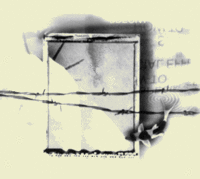
我的第一份打工,是在學校旁邊的便利商店。從19XX年9月到翌年的寒假,每週固定上三天晚班。
我生長於商人之家。爸爸在一棟商業大樓工作,熱中於股票投資;媽媽本來是中學老師,生下我和妹妹後辭去教職,起先開一家麵攤,搬家後改經營文具店。雖然如此我和妹妹卻對經商毫無興趣。大學念的科系與商無關,除了儲蓄對理財一竅不通。就隔代遺傳來說,我們就是屬於如伏流消失的世代吧。
文具店在我高一時結束營業。貨品全部出清後,店面變得空盪陰暗。我還記得剛搬來時,嶄新的玻璃櫥子在午陽迴照裡閃爍明亮的情景。為什麼它們突然就變得如此破舊?好像在檔案底層慢慢腐蝕的病毒,我竟然一點也沒發覺。等到舊櫥櫃運走,我曾經在這裡居住的記憶彷彿也被挖空。慘白的牆壁、四方的格局,有如荒棄十年之久的廢墟。我們站在路邊,等搬家公司的卡車繞到前面,就像且行且過的路人。這種疏離的感覺,不知道為什麼,或許我在這裡從來沒有幸福的回憶吧。
不過在文具店裡,被各種雜貨包圍的感覺,零碎的結帳,以及客人進出的氣流,那種生活還是以某種方式影響了我。突然產生「我應該來這類地方工作」的想法,只是這些暗流匯積推動的結果。
◆
店長是個瘦瘦高高的中年男人,下巴有著刮不乾淨的絡腮鬍,愛嚼檳榔,口齒不太清楚,戴著一副不適合他的金邊眼鏡。
上班頭兩天我只負責補貨,下班前掃地拖地,給蒸包子機和茶葉蛋鍋加水。兩天後我開始練習收銀。店長先教我不同商品別的按鍵,一百種換發票的技巧,和預備金的清點。收銀交給我負責後,店長繼續點貨訂貨,在辦公室和賣場間進進出出。他拿著一本大簿子在每個區櫃前清點劃計,嚴肅的表情像是動物園裡的台灣彌猴。
平常會碰面的還有副店、大夜班的小P和其他幾個工讀生。我不容易適應新環境,認識人的速度也相當緩慢,更不喜歡和別人打交道。因為是工作伙伴所以要彼此熟悉,我對於大家的感覺就是這樣。
副店和我一樣是考生,今年要考二專。我本來以為她比我大二、三歲,當她說:「我是6X年次」時真的讓我嚇了一跳。
副店和店長充滿對比的色彩。首先她是個美女,而且是個很胖的美女;此外她口齒伶俐、個性豪爽衝動、人緣很好、工作能力很強等等。
這兩個人就像在整理唐詩和宋詩的相異處,可以做出一張互為對照的表格。
她最常做的事就是拍一下我的肩膀,用全世界喇叭同時響起的聲音說道:「賣場的貨補了沒?茶葉蛋的水加了沒?地板掃了沒?拖了沒?再混啊,工讀生的錢可沒那麼好賺!」她會隨時盯著我補貨、打掃、加水,讓我忙碌地像是沒有終點的旋轉木馬。
我離職半年後,副店和其他工讀生先後離開,接著店長也不知去向。
副店考上二專後,就到隔壁的咖啡店打工,那個老闆跟她很熟,常常到店裡來借新的雜誌,向我揮揮手就走出去。起初我不知道他們的默契,還以為他是會和店員打招呼的新品種小偷。
除了咖啡廳老闆,副店似乎還認識很多客人。「店裡生意怎麼樣?」、「上次的事解決了嗎?」、「你的感冒有沒有好一點?」諸如此類的話她常常掛在嘴邊。有時候她也會跟我說:「剛才那個女生很漂亮吧,他是在美容院工作的,就是轉角那一家。」口氣熟稔地好像剛從那邊洗頭回來。
「你怎麼跟客人那麼熟?」有一次我好奇地問道。
「熟?我根本不認識他們,只是常來買東西就打個招呼。你地掃了沒?再混啊!」副店大剌剌地說道。真是讓人意想不到的答案。
我的打工就在一緊一弛的環境裡,沈默而緩慢地進行著。
◆
文具店結束營業後,媽媽跟著做了幾年股票。妹妹考上大學後,她也到爸爸工作的大樓作會計。
媽媽開始上班後,白天就只剩我一個人在家。我習慣睡到大家都出門後才起床。每天早晨在假寐間,聽到大門上鎖的聲音後,才像鞋匠小矮人一樣地推開房門,來到客廳裡肆無忌憚地走動。
那時暑假還沒結束,起床後我會先到附近的游泳池游一千公尺,然後曬半個小時日光浴。回來的路上買紅茶跟漢堡當早餐,之後就以聽音樂、看小說、上網路的方式,消磨下午的時間。
類似獨居的感覺,只要到了傍晚時分,家人陸續回來就會煙消雲散。房子再次熱鬧起來。嘈雜的電視聲和炒菜的香味四下瀰漫,微波爐發出嗡嗡的運轉聲,時間一到就會嗶嗶嗶地叫。妹妹會問一些跟自己無關,只是單純讓爸爸大發闊論的問題。
接下來我就必須出現在餐廳,好像時間一到就從咕咕鐘冒出來的啄木鳥,盡到義務後又要回到小小的黑暗當中。
「怎麼見到爸爸都不會叫呢?」
「爸爸。」
「你好像叫得很痛苦。」我有嗎?「好久都沒有看到你了。」
「還好吧。」我幾乎每天都在家裡吃飯啊。
「你是不是把家裡當作旅館一樣,只是用來吃飯睡覺的地方。家裡真的那麼沒有溫暖嗎?」
「不會啊。」為什麼一見面就要說掃興的話呢?
「你也長大了,要多幫家裡想。家裡經濟情況不好,你們就不要隨便亂花錢。」還不都是你玩股票賠光的,「你如果太閒,就去打打工,不要整天沒事幹。」
就這樣,布咕、布咕、布咕、布咕、布咕、布咕、布咕,整點報時結束。
◆
店長還沒結婚。他已經超過三十五歲,也沒有交女朋友的跡象。這似乎和他的態度是否積極沒有關係,真的會有女生(或男生)喜歡他這種人嗎?我想這在他過去的人生也是寥寥可數的吧。
上班第四個禮拜,聽到最可笑的流言是「店長對我有意思」(或者「店長跟我是一對」)。
「你跟店長不錯嘛,」副店語帶諷刺地說道,「他每次看到你都會特別開心。」
「哪有啊?」那是因為他看到妳就開心不起來吧。
「你們單獨在店裡的時候都在幹什麼?很可疑喔。」她斜睨著我。
「太誇張了吧,在店裡能幹什麼?」這個女人真是越講越離譜,「妳也多關心你們店長,趕快幫他推銷出去。」
「像他那樣子啊,還是省省吧,我才懶得管他。」副店一邊喝紅茶一邊說道。她是我們當中唯一有伴的,男朋友在一家電玩店做事,兩人是專科同學。一想到像副店這樣的女人,將來也有結婚的打算,眼前就好像出現一片荒涼的景象。
下班前店長突然問我:「你有騎車嗎?」
「有啊,幹嘛?」我正把晚班的收入封好,準備投入金庫。
「我老公有事不能來接我,你送我回去好不好?」站在一旁的副店說道。
「妳住哪裡啊?」
她說了一條街名,「那離我家很近嘛,我就順便送妳吧。」
「那就拜託你了,你要保護她喔。」
副店聽了大笑道:「你說錯了吧,我保護他還差不多。」
「隨妳怎麼說吧。」不過應該沒有歹徒想動你的腦筋,我沒好氣地想著。
一上車副店就叫我坐後面。十一月的夜風透著初冬的蕭颯,坐在前面的副店就像一堵溫暖的牆。不知道是否機車馬力不足,她騎得很慢。我們隨便聊著,店裡的事、家裡的事、報紙上的新聞。因為騎著夜車若是光聽引擎的聲音,會有格外淒涼的感覺。
「你家裡一定很嚴吧。」副店突然說道。
「妳怎麼知道?」
「感覺吧,我的感覺一向很準喔。」
「與其說是管教嚴格,不如說是我爸他根本不信任我,也不瞭解我的想法。」
「你們家也會管你嗎?」我反問她。
「剛開始也會管啊,後來我跟他們吵了幾次,也就沒有人管我了,大概是死心了吧。」
「我也試過,可是沒有用。上一次才吵完,下一次又要重複同樣的問題,我已經懶得溝通了。每次我想表達什麼,我爸就會說『長大了就可以不聽話』、『翅膀長硬了就想飛了』,根本談不下去。」
車子在紅綠燈前停下,四周已經十分寂寥。車子一起動,身邊好不容易凝聚的暖氣瞬間又被衝散,讓我不禁打了個哆嗦。
「我家人也說過同樣的話,你知道我頂什麼?我說『翅膀長硬了就要飛啊,」副店大嚷嚷地繼續說道,「不然長翅膀幹嘛!』」那聲音宏亮地彷彿能傳到世界的盡頭。
◆
年底爸爸又為了我一個禮拜太少在家吃飯及常常晚歸生氣,拿出家庭不是旅館的說法。
「人家是爸爸回家吃晚飯,我們是兒子回家吃晚飯。」
「我是去打工,又不是去玩。」
「你可以選白天打工,幹嘛要選晚上?」
「白天我要上課啊。」
「那你就不要去打工了,明天就不要去打工,打工多少錢我給你。」
「哪有人說辭就辭,店裡規定要提早兩個禮拜辭職。」
「那你下個月就不要去打工!」
「當初是你叫我去打工,現在又教我不要去打工,我已經適應店裡的工作情形,你不覺得這樣很霸道嗎?」
那天的談話不知如何結束,和他的談話總是沒有交集。我們有如相對的〒箭頭,雖然由同一源而出,思想上卻相背而行。
稍晚妹妹到我的房裡,似乎有話要對我說。
「有空嗎?」
「有話就快說吧,我要睡了。」
她站在門口聲音壓得低低的,大概怕被另一個房間的爸爸聽見,「你以後就不要那樣跟爸爸講話。」
「你不覺得爸爸很過分嗎?」
「可是你每次吵完,爸爸就會罵媽媽,你也幫媽媽想一下。」
我沈默了一下,坐起身來說道:「我幫媽媽想,誰來幫我想?當初她會嫁給這種男人,現在也是她自找的,能怪誰呢?」
尷尬在我們當中無聲地蔓延,像是整個六月的梅雨,終於她先打破沈默,「你只會想到自己,都沒有想到我們。」
我愣了半秒鐘,把燈打暗被子一蒙,「妳說完了就去睡覺,記得把門關上。」
我聽見門被關上的聲音,黑暗當中只剩下我一個人。我睜開眼睛,好一會兒從那似乎什麼都沒有的漆黑當中,浮出無限空洞的輪廓。
◆
對工作熟練後,和店長講話的時間反而變少了。就算他早點結束盤點到櫃檯來抽煙,我也會因無話可說的尷尬,更不知道應該講些什麼。我想這是因為有人在旁邊,就會讓我有「應該說些什麼」的想法。他對於兩個人一直保持沈默似乎並不在意。
店長給我的感覺就像沙漠,而且不是「英倫情人」或「遮蔽的天空」裡,美得不可方物的風景。他像教科書上,一翻開就令人有乏味感的圖片。在店長身上完全看不到夢想或是對未來的計畫等,即使虛假也會讓人閃閃發光的成分。
有一個作家寫過:「一種是本來就很平凡的人,一種是故意讓自己變得平凡的人。」
通常八點過後賣場已經整理好,客人也還沒有上門。在好像螢幕保護的真空期,我會偷閒翻閱當天的報紙。那時正熱門的新聞,是一間便利商店深夜被搶,工作人員為了阻止歹徒不幸被刺死。歹徒很快就被抓到了,總共不過被搶了兩千多元。
「你有看到新聞嗎?」
「什麼新聞?」
「這裡啊,」店長指著晚報,「有一個便利商店的店員被歹徒刺死。那個年輕人真不值得,才多少錢,要搶就讓他搶,幹嘛要逞英雄?」
他又問我:「現在如果有人來搶劫,你該怎麼應付?」
我想了一下,「只好讓他搶了。」我可不想被殺掉啊。
他笑道:「對啊,就讓他搶。我們這邊都有錄影,跟警察局都有連線。你什麼都不要動,通常這些歹徒都很緊張,搶了收銀機的零錢就跑,也搶不了多少,公司都會負責。」
他稍微停頓了一會兒,「等歹徒走了以後你再打電話給我,或者給副店,如果都找不到就打給鄰店店長,他們會過來處理。電話都在辦公室門上,你知道吧?」店長一口氣講完所有的重點,流利地好像換了一個人。
「我只是告訴你該怎麼做,」他一邊說道一邊把煙捻熄,「你們年紀都很輕,都是社會的人才。」
我看他那副惋惜的表情,真覺得這是一個好人。或許是我的態度通常很冷淡,才覺得他的想法特別溫暖吧。這樣的人是經過了哪些過程,才變得如此貧瘠呢,那大概跟冷凍食品經過脫水壓縮的程序一樣吧?我這樣的人才應該有這樣的命運。
一瞬間店長和父親的形象,就像手繪描圖紙般地交疊在一起。他們沒有夢想的人生,一如從南到北毫無特色的小鎮,居然會如此相像。
◆
下班後我通常不會直接回家,先騎著機車四處閒晃一番。在深夜騎車有種被釋放的感覺。只有這樣的漫遊,才能體會生命的無目的性和流動的感覺。即使如火花一般地蒸發,也不想用手中的時間,向世界證明什麼。抱持這種想法,我好像正以光速和每個人遠離。但即使終其一生的時間,我也只能前進到比現在稍微遠一點的地方吧。
SAPARATE、SAPARATE、SAPARATE,重複著這個音節,在我的身體裡好像就要出現裂縫。它從我的腦門貫入,穿透咽喉、心臟、腸胃,還有肛門。
每次一有這種感覺,就會有我生來就應該做工讀生,而且一輩子最好都以此為業的念頭。
◆
一上班店長就叫住我,「你下個禮拜有沒有空?有工讀生要請假,想要請你代班。」
我考慮一下,「好啊,反正那天我沒課。」
「太好了,那你九點來接小P的班,白班的工作跟晚班有點不一樣,我再請副店教你。」
於是禮拜二我起了個大早,不到八點半就到了公館。我先在校園裡繞了一圈,朝著和人群完全相反的方向,漫不經心地遊走。路上已經有很多趕著上課的學生,大樹下有練氣功和太極拳的人們,籃球場上也不乏鬥牛的人潮。一切在陽光下顯得朝氣蓬勃,彷彿有再多的問題,只要在這種天氣裡曝曬一下就會煙消雲散。
九點整我走進店裡,和小P互道早安。我換上制服清點預備金,接手早班的工作。一大早其實沒什麼人,上班上學的人潮已經過去,從玻璃窗望出去巷弄非常冷清。除了有個女人一口氣買了19份報紙,她大概是廣告公司的員工吧。之外就只有零星的居民。小P一時還不想走,我們斷斷續續地聊天。一會兒副店來了,一進門她就大聲嚷嚷著:「外面那輛機車是誰的?小P你去挪一挪,不要擋住門口。」
小P很快地走出去。然後她走到我旁邊,「再混嘛,又想要偷懶了。」
「可是沒有客人,店裡也很整齊啊。」
「哎喲!會頂嘴啦!」
「吃早飯了沒?」她又問道。
我搖搖頭。
「要吃什麼?」她走進櫃檯斜靠在冰櫃上看我,神情顯得相當愉快。
「麥當勞好了。」
「我要滿福堡加蛋,還要柳橙汁。」
「我不要蛋!」小P正好從外頭走進來。
「你要什麼自己選,去買吧。」副店從皮包裡掏出兩百元,「這些應該夠了,不夠就自己貼吧。」
我買了三份早餐,在店裡和大家一起津津有味地吃著。能和別人共用早餐,讓我覺得彼此格外親近。就算沒聊過什麼的小P,此刻也好像相當熟悉的朋友。
雖然只是平凡的瑣事、平凡的時光,沒有什麼讓人記住的深刻印象,然而早晨把人沖淡地沒有什麼防備,我喜歡起初還有點混亂的感覺。
白班的工作比較瑣碎,要進貨、清點、退貨、包新雜誌、退舊書、在不同的單子上簽字。走道上到處堆著來不及上架的貨品,我幫副店先把礦泉水搬到倉庫,再把洋芋片、餅乾、海苔、泡麵一一上架。小P不知道何時離開,當我把回收的保特瓶放到辦公室的時候,才發現他已經不見了。將近中午人潮聚集,店裡顯得一片混亂。貨品上架後,副店要我把瓦楞紙箱壓平,堆到辦公室門口讓老伯收走。我趁著空檔趕快壓扁幾個箱子,又要衝回櫃檯幫客人結帳。副店一忙起來臉上就沒有任何表情,我也盡量不和她的視線接觸。
三點過一刻店長上班。他看起來很沒精神,大概才剛起床吧。我跟他打招呼時他也沒有發現。
「今天怎麼會是你?」店長看到我,好像在台北街頭發現無尾熊般地驚訝。
「我來代班啊。」
「啊,還好吧,比晚班要忙一點。」
「還忙得過來。」
「今天算你好運,」站在一旁的副店說道,「我告訴你白班可沒有這麼輕鬆。」她一面結帳一面用貓似的眼神看著我。我無聲地微笑,脫掉制服準備下班。走道上仍有一堆東西等著上架,不過那已經和我無關。我把紙卡插進打卡鐘喀噠一聲,多出來的代班印在上頭就像一個走調的音符。
◆
過幾天小P就出事了,那天我剛好沒班,隔天下班的時候店長才跟我講:「小P不會來上班了。」
「怎麼了?」我驚訝地問道。
「他昨天跟別人打架,就在前面的街上,打得很凶,連管區都過來。」
「那小P有沒有受傷?」
「他們三個圍毆對方一個,怎麼會受傷。對方被打得流鼻血,後來全部都被帶走了。」
「真糟糕。」我竟然沒有看到實況。
為了請新的大夜班,店長和副店在意見上發生摩擦。
「你們家店長很過分耶!」
「等一下……什麼時候變成『我們家』店長?」
「本來就是你們家店長,不然還我們家店長嗎?」副店揮動手腳地說道。
「他哪裡又得罪妳了?」
「還不是大夜班的事情。前幾天有人來應徵大夜正職,我本來想錄取,結果你們店長說不要,他說要找小P回來上班。他都搞不清楚,大夜本來就該找正職,發生事情才好交代。而且小P做不了多久就要當兵,到時候又要再找!」她激動地瞪著我,下唇高高地噘起。
「那幹嘛要找小P回來?」
「還不是因為小P的薪水比較好談!」
結果不到一個月小P就回來上班,副店和小P還是跟以前一樣熟絡,好像沒有發生過反對店長找他回來這件事。
店長和副店間的爭執,都是單方面的不滿。店長從來沒有提過這種事(或許他根本沒有發現),還常常在我面前誇獎她。「她很有能力,在這家店也待的比我久,很多事情我還要請教她。」這種情形跟反應過度的女人,與遲鈍男人的組合一樣可笑。
和店長的視而不見相反,我即使勉強自己去適應周遭的環境,不能接受的部份卻不斷地反彈擴大。好像長期穿著不合腳的鞋子,遲早會把腳底磨出水泡,完全沒有「相處久了就能慢慢習慣」這種事。
另一個作家寫道:「一生只見幾次面的人像計程車;常常聯絡的朋友像每天搭乘的公車。」
半年以後的便利商店完全沒有我認識的人,彷彿經過了半個世紀更迭的古老城堡。曾經在這裡的人,都是一點上往外幅散的射線,繞著球狀的命運前進,什麼時候會再見面呢?
然而我是商人之子,即使也有淡淡的感傷,對於這些轉變的習以為常,就像與生俱來似地。做了半年的工作、讀了四年的學校、相處二十年的家人,這些和每天要經過的街道一樣,只是我人生通過處的風景。
◆
提出辭呈的時候,店長顯得非常為難,「怎麼突然要辭職,不是做得很好嗎?」
「馬上就要考研究所了,我想專心準備功課。」
「適應不良嗎?還是工作上有什麼問題?」我搖搖頭,店長沈默了一會兒,「你再考慮看看吧。」
按照計畫我會在月底辭職,從郵局領到最後一次薪水。雖然離開周旋在收銀機和賣場間的生活,還會有一段揮之不去的影子,一如睹物思人的舊戀情,雖然結束了,卻好像還留在什麼地方。
「你真的辭職了,」妹妹說道,「你也知道爸爸的個性,要他改變不是那麼容易。」
「我才不想等他改變,」我躺在床上一邊看小說一邊說道,「反正時間到了,將來會變成怎麼樣,都是他自己造成的。」
「你以為我就喜歡爸爸的作法嗎?但畢竟大家都是一家人啊,為什麼不能互相體諒?爸爸不懂,你也跟著他一起賭氣嗎。」
「爸爸在的時候曲意順從,等他不在了才大鬆一口氣,這就是妳所希望看到的嗎?」
雖然嘴巴上這樣說,但我對妹妹的話並非毫無感覺。對於父親,我也有過單純的孺慕之情吧。只是在不斷重複的爭吵、反抗、叛逆中,那種情感消失了。如果不能相互瞭解,即使是有血緣關係的家人,也會像持續凋零的青春一樣,逐漸地變得不復記憶。
我們有不同的信仰,妹妹相信「凡事會更好」;我相信「災難一定會過去」。其他人呢?即使表面上說出一樣的話,內在的含意也是相當不同;相反的,在表面上完全不同,卻可能在意外的地方交會。
有一次我問副店會不會和現在的老公結婚。
「會吧,等有了經濟基礎。」
「結婚以後呢?」
「生小孩啊,你不是也一樣。」
「我不結婚。」
「不結婚,你同性戀啊?」副店諷刺道。
「要妳管!我討厭小孩啊,只想要同居就好了。」我在態度上也不甘示弱。
「等你老了就會知道,一個人活著實在太寂寞了。」
◆
最後一天上班店長比平常多話。
「辭職以後要幹嘛?」他問道。
「先休息幾天,然後要準備考試。」
「加油!你一定沒問題的。」
「不要這樣說,我會心虛的。」我笑道。
「像我唸書就不行,你們會唸書的就好好加油。」他靠著櫃檯抽起煙來,他抽煙的樣子也是廣告上絕不會出現的。
「考完試如果想要回來可以再回來,你也知道,訓練新工讀生很麻煩。」
「我會考慮的。」
「以前我對大學生沒什麼好印象,不過你來工作之後,讓我的觀點改變了。」
「我沒那麼厲害吧?」我尷尬地笑道。
「你不要笑,我是說真的。」
我長吁了一口氣,像我這樣苟且偷安的人生觀,也只能行進至此了吧。再下去就會發出沉重的廢棄聲,逐漸失去原有的光澤,沉默地在邊緣地帶拋錨。
第三個作家寫到:「養兒女不如養狗。」
◆
離職的第一天,我終於在晚飯時間到家,卻不想要進門,一個人坐在機車上,面對三樓的陽台發呆。
我想像現下家裡的情景。媽媽正在煮飯,爸爸依然坐在客廳看電視,妹妹在房間裡準備考試。明亮的燈光溫柔地包圍著每個人,在裡頭的一切和外面的黑暗無緣。還有一個房間空著,那是屬於我的位子,所以我拿起我的這片拼圖,準備放進那個小小的缺口。
然而怎麼樣也拼不回去了。
我搖搖頭說聲抱歉,讓他們繼續保持目前的狀況。面對工讀無止盡的徒勞緩緩浮現。在某個地方總是會有這樣的情形,現在和過去,現在和未來,最後都會變成無法歸檔的風景。它們被留在事相地平面的彼方,一如掉進黑洞裡就逃不出來的光線。如果還有機會,它們會不會像嘔吐一樣,被丟到另外一個宇宙呢?
我只能希望,希望那是一個適合夢想生存的地方。
入冬後的天色很快地就暗下來,微昏的夕陽還在樓房後方,拉成頭頂越來越沈重的暮色藍。街燈發出細微的聲響定時點起,好像倒帶似地慢慢變亮。


0 Comments:
Post a Comment
<< Home